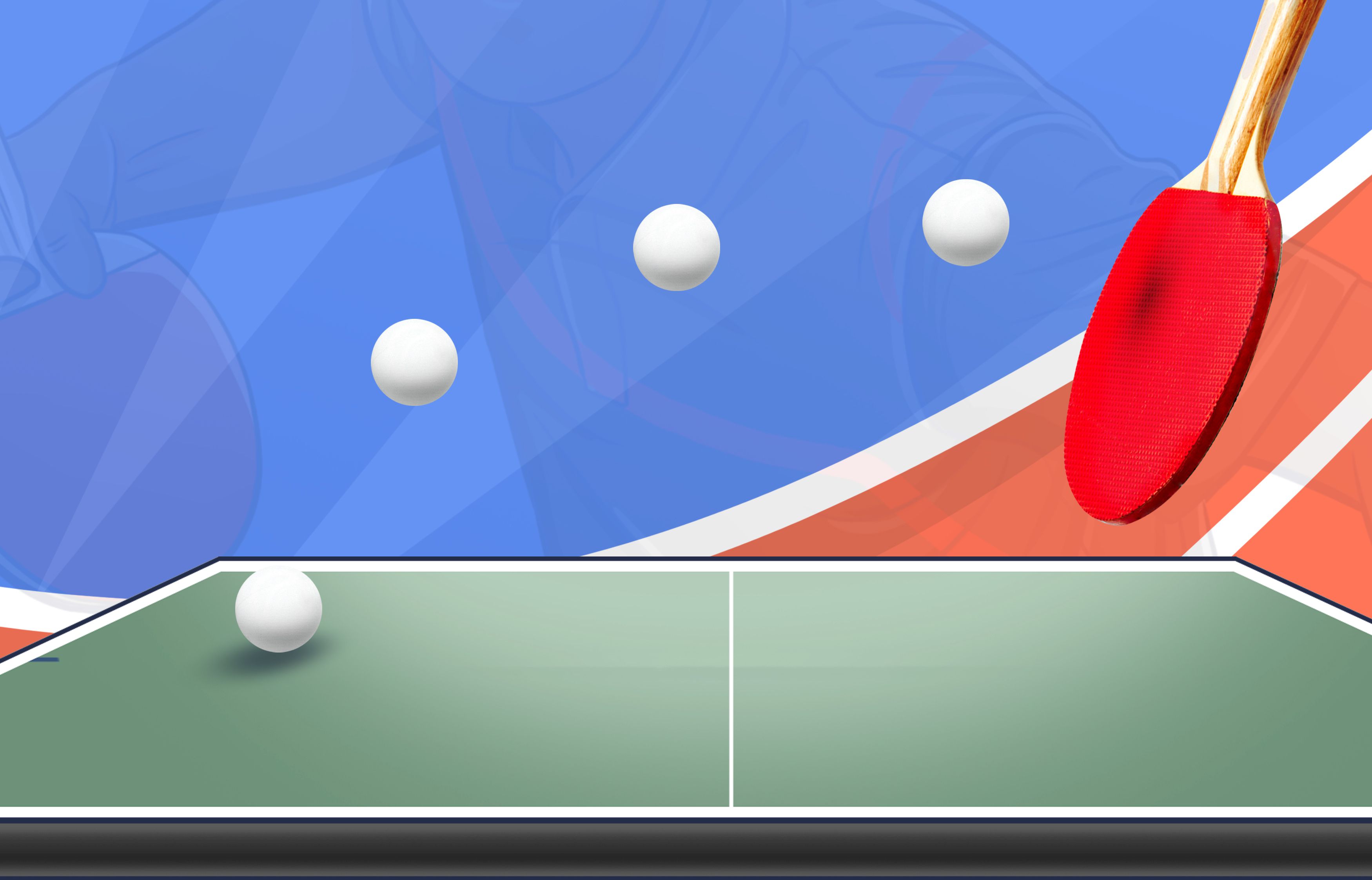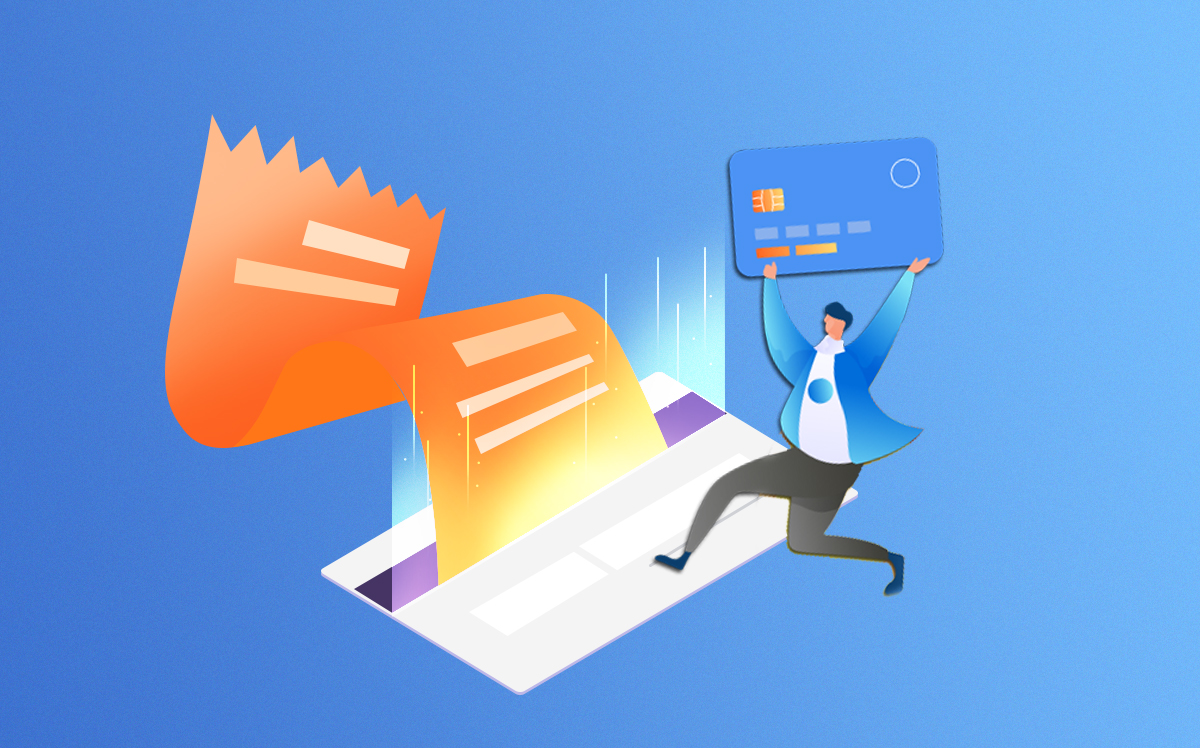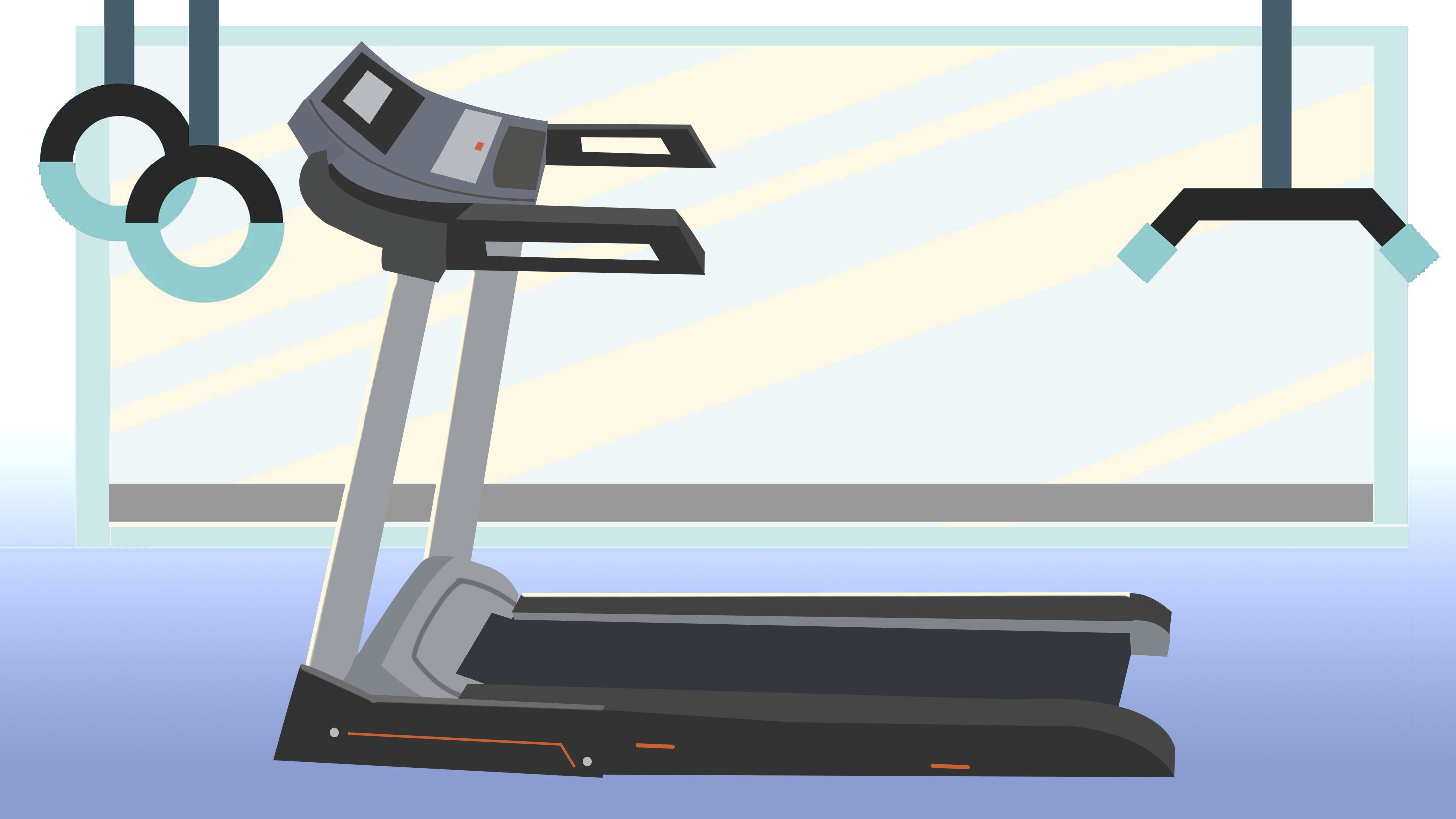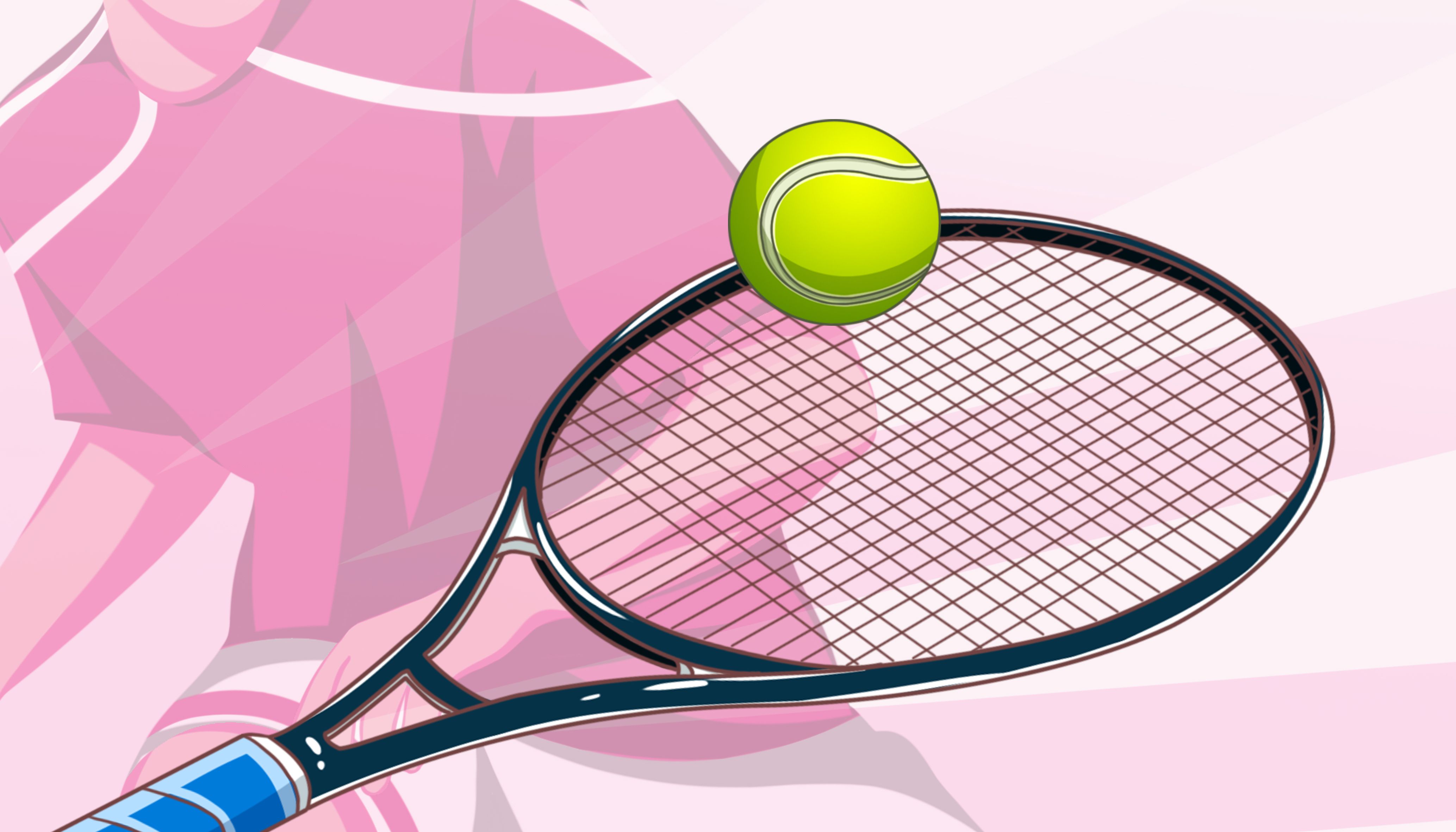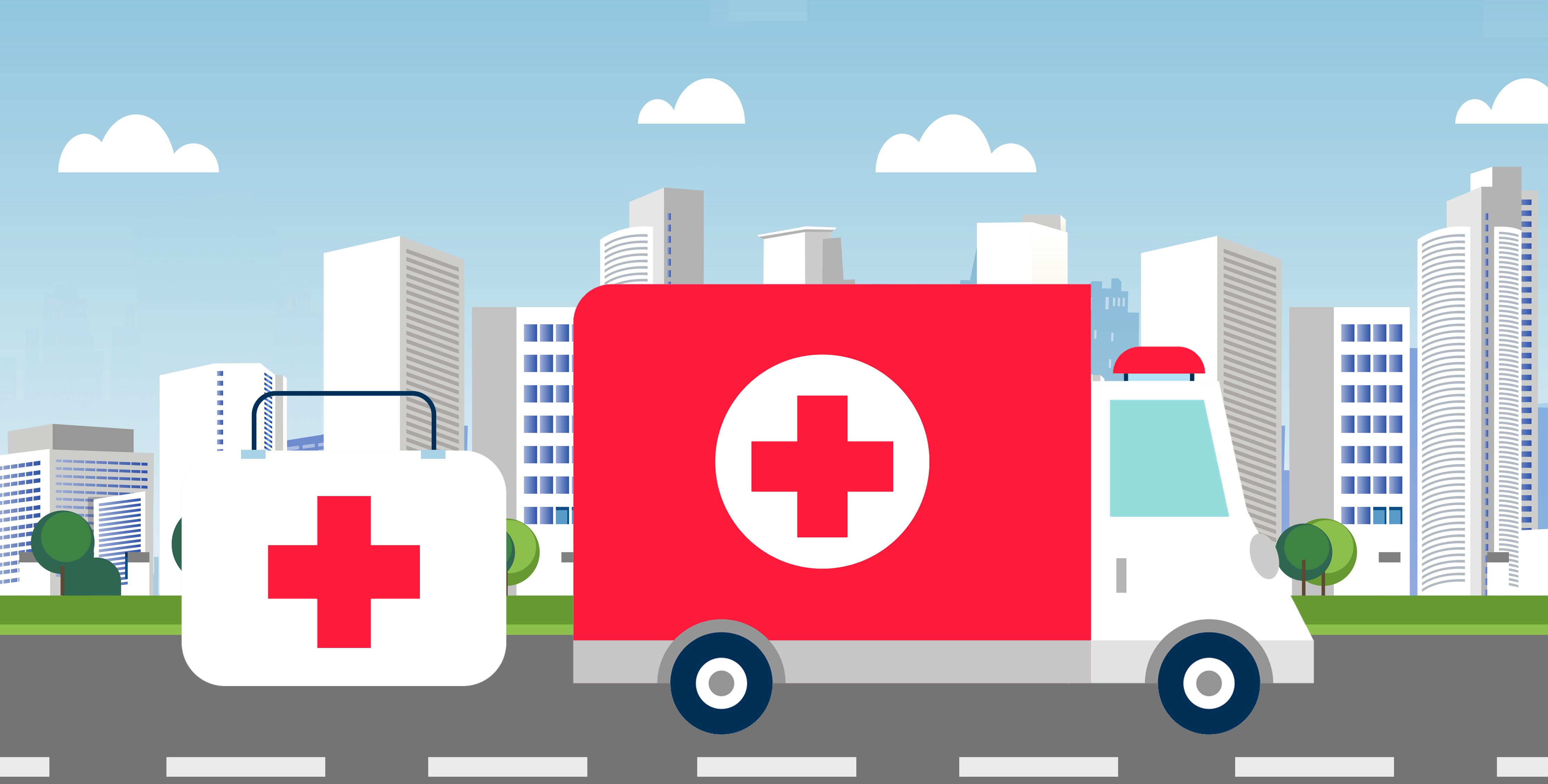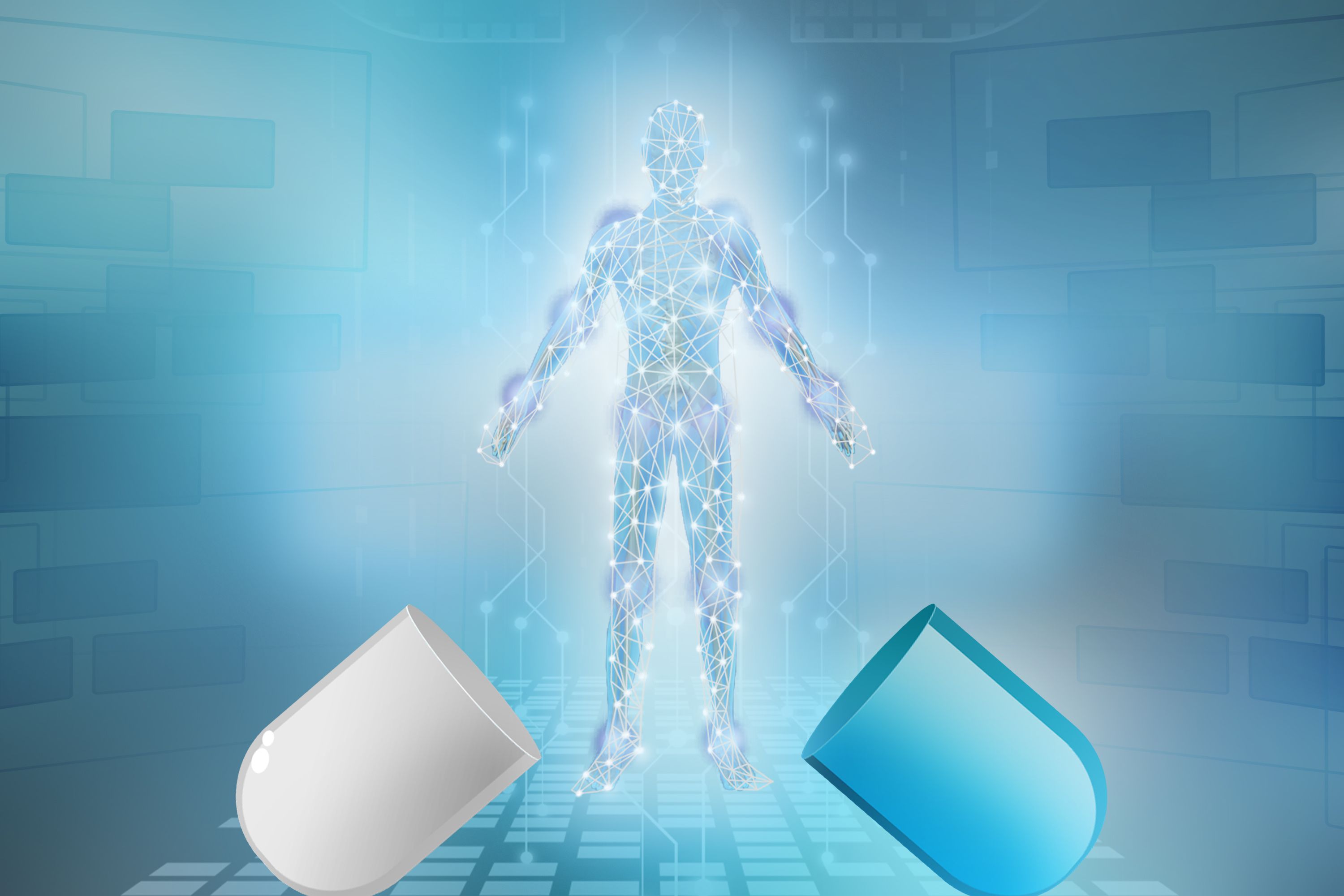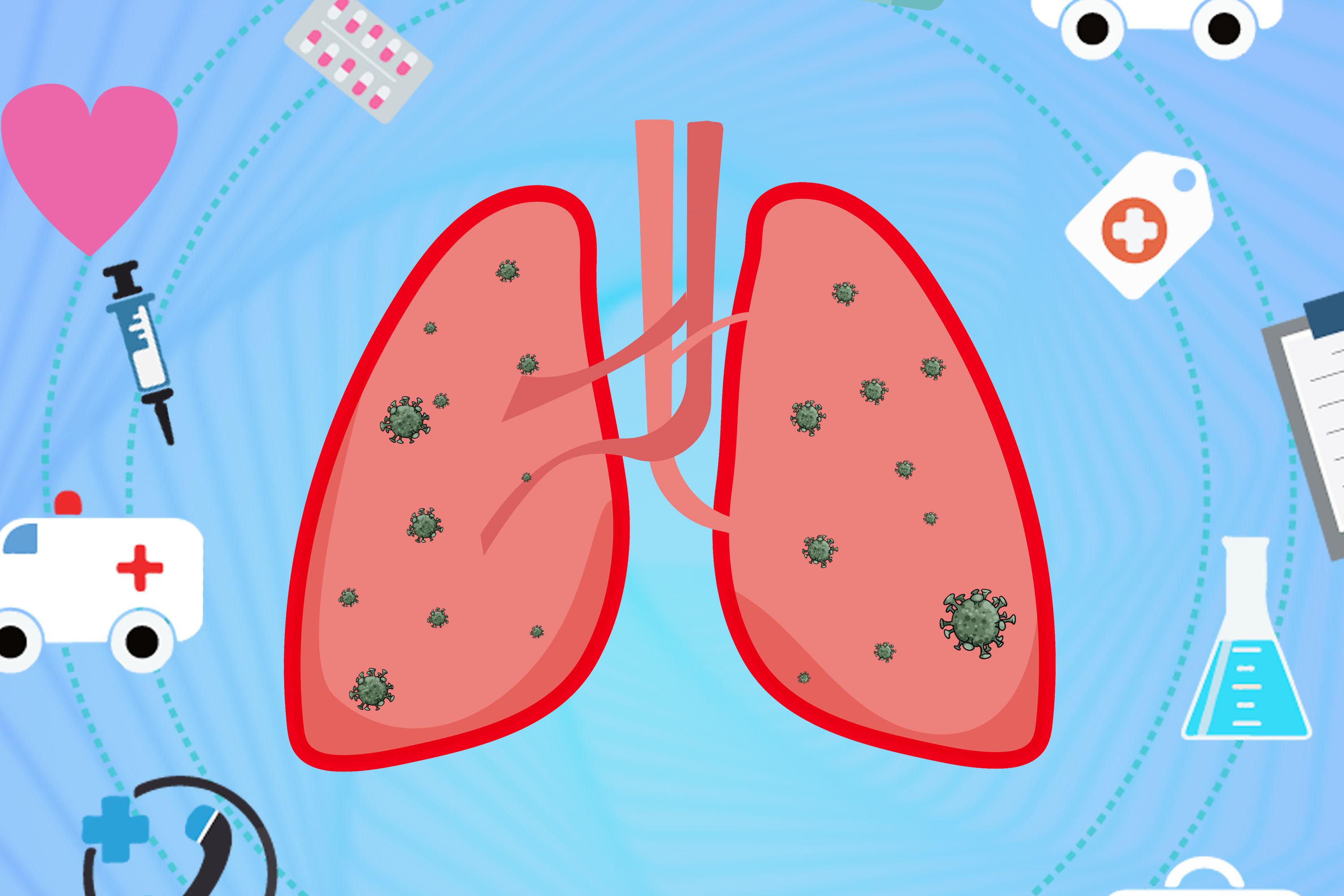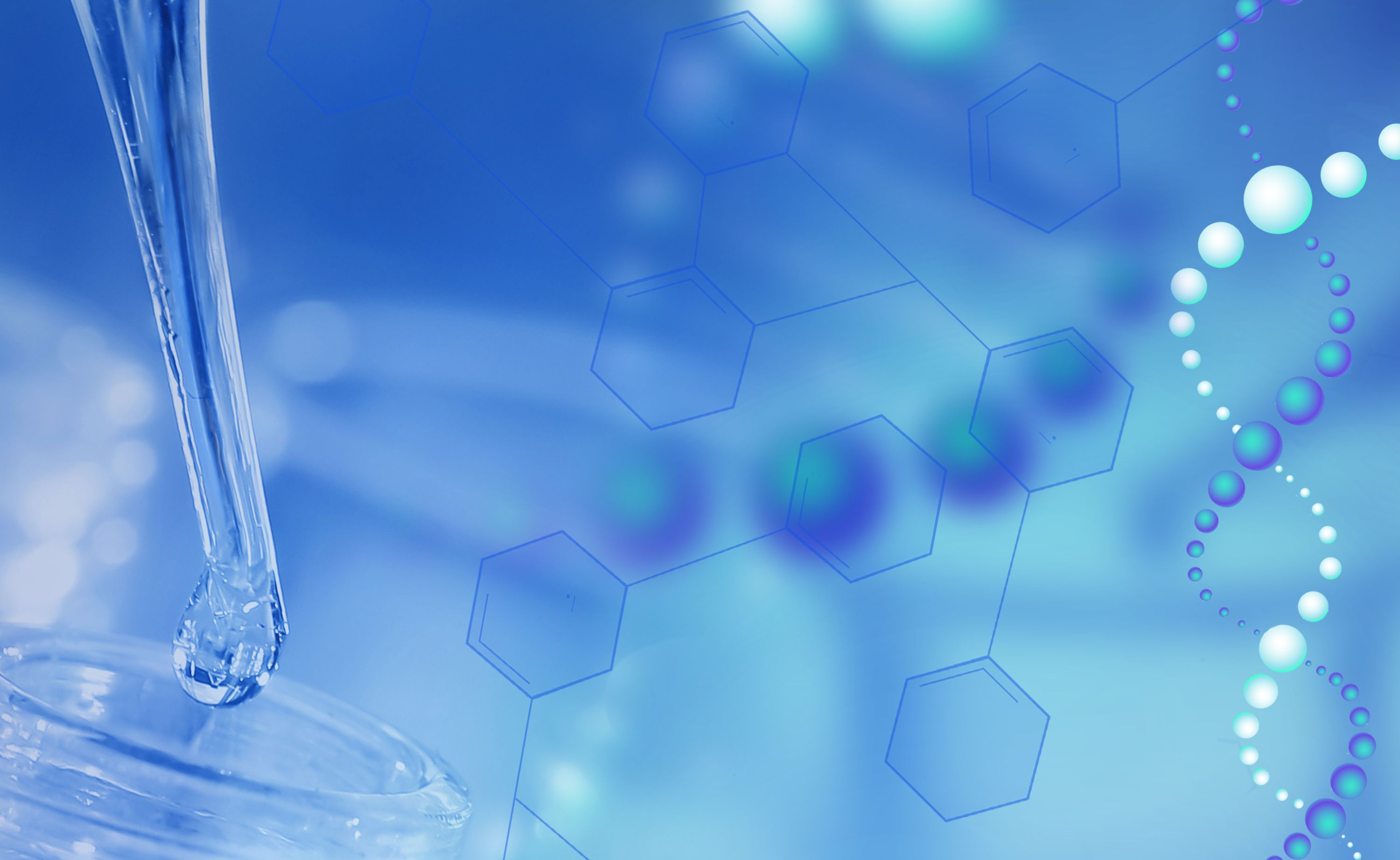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在一次摄影展览上,一组呈现淞沪铁路如何慢慢变成现在的上海轻轨3号线、4号线过程的作品,引起作家周嘉宁的极大兴趣。她是地道的上海人,经常坐3号线和4号线。这个摄影展提醒她:自己使用这两条地铁十几年,从来没有想到它的前身会是什么。在复旦念书的那几年(2000年到2007年),宿舍和校园之间有铁路穿过,一些很缓慢的绿皮火车会穿过学校。此刻她才意识到,当时穿过学校的这段铁路,正是淞沪铁路。
2022年9月1日,在北京单向空间书店,周嘉宁在她最新小说集《浪的景观》首发分享会上,在与电影《爱情神话》导演邵艺辉、受不少年轻人喜欢的播客“随机波动”主播傅适野的对谈期间,详细讲述了这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上海,作为她的家乡,这个城市的历史、发展,与她写小说的灵感触发点、内在动力都密切相关。但看完小说,又会发现,与其说她关注城市规划,不如说她心心念念要表达和呈现的是,时间流逝的形状,青春岁月里,一些特别的记忆。事实上,这种性格、兴趣、关注视野,也决定了周嘉宁的小说有一个一贯的主题——时间带走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
周嘉宁
“千禧一代中篇三部曲”
《浪的景观》是周嘉宁长篇小说《基本美》之后出的全新中篇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她近三年写的三个中篇《再见日食》(2019)、《浪的景观》(2021)、《明日派对》(2022)。小说里人物存在的时间是过去20年。这三个故事的背景大概都是千禧年。第一篇是从1995年延续20年的故事,后两篇发生在2000年或2003年的样子,现在都是20年左右的时间。但阅读的时候会觉得和当下有一种奇妙的共振感。因此也被称为是“千禧一代中篇三部曲”。
使用扎实、精确、节制的叙事方式,周嘉宁勾勒出全球化语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的内心某些特质。书中地点从偏远的美国小镇,到南京某处名为“防风林”的地下室,从挤满罗大佑歌迷的南下列车,到已不复存在的上海迪美地下城,周嘉宁书写时代浪潮中的友谊、爱情、梦想,以小说的形式,为读者的内心提供“一块干净明亮的地方”,以至于有人说她用文学“做21世纪初的时间考古”。
说到21世纪初,周嘉宁特别提到2001年。这对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那一年,上海女孩周嘉宁,跟好朋友趁暑假一起去北京玩。那是她第一次到北京。到旅馆当晚,恰好是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一天。“公交车都停在了马路边上,公交车都是空的,但是车顶上爬满了人,拉着各种的横幅,整晚地狂欢。这种整晚的狂欢在我大脑里面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印记。我之后整个青年时代是从2001年申奥成功那一天开始的,那一天所有人都在狂欢,不认识的人都在打招呼,带给少年的幻觉太过于强烈。我的人生是带着这样的一种快乐的底色开始的。”
《再见日食》的主角设定为一个名叫满岛拓的日本年轻作家。20年前,他曾在美国爱德华州参加一个写作班,那里面有世界上其他国家来的很多年轻人,大家共度一段时光。他认识并爱上其中一位来自中国的女孩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大家在这里有一种情谊的心灵的连接,像做了一个美好的梦。时隔20年再访佩奥尼亚小镇,与青年时代的友人们重逢。
本雅明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做过广播员,他看待广播媒介的方式是将其作为一种大众教育手段,并引导其形成“判断力训练”。 在《明日派对》中,周嘉宁写的故事可算是播客时代对电台时代的进行一次回望:在2000年罗大佑在上海的演唱会上,两个女孩因同为电台主持人张宙的粉丝而相识。后来她们一起参加比赛,一起做节目、玩乐队,一起度过一段自由的时光。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评价《明日派对》里的年轻人,“这群年轻人又显然有着某种无形的积极,仿佛内在的眼睛睁开,看到了世界深处的独特活力,外在的任何羁绊都不足以缠缚住他们抵达彼处的脚步……小说中那轻微的颓然感没有变成浑浊的消极,反而因为洗净了积极中通常内含的焦躁之气,显现出某种值得珍视的内在清澈。”
因“新概念”成名20年
感念其是“第一份巨大的礼物”
周嘉宁高中时因参加第一届和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被复旦大学录取。19岁就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流浪歌手的情人》。2007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毕业。2008年,她去了北京,与张悦然一起创立文学MOOK《鲤》,2010年回上海成为专职作家。勤奋和天分的调和,让她已成为一个技艺纯熟的小说家——语言精准简练,但又有足够的诗意。既不是铺张渲染,又不是纯以情节取胜、没有光芒的通用语言。在同龄人群体中,认识周嘉宁的人可以感受到,在她身上,有一种突出的“文学少女”气质。过着简单的纯文学翻译、小说写作工作,其余时间会运动,阅读,或者沿着苏州河走很远,观察上海的生态环境。
周嘉宁
距离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上崭露头角已经过去快20年了,如今,周嘉宁已是新概念的评委。不像一些人因为新概念成名,但却不太愿意提这个往事。周嘉宁很坦诚,她始终将新概念的获奖视作命运给予自己的“第一份巨大的礼物”,“为什么这些年来大家反反复复还在提新概念,今天的记者还是会问起这个问题?这说明新概念不仅影响了我,还影响了所有人,也影响了记者们,影响到媒体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角度,影响到一代一代读者的阅读评判和选择。”
曾有较长一段时间里,“80后”作家是一个响亮的标签。如今这个词正在褪去光环,失去新闻效应。这群同代际作家们也逐渐分散在不同的领域内。周嘉宁是依然在进行纯文学写作的一员。
在其与张悦然一起创立的杂志《鲤·我去二〇〇〇年》中,策划了一期80后作家们给予逐渐远去的少年时代的一次集体性省察,试图共同追溯当时的经验如何影响了现在的自己。其中,周嘉宁选取了一次台风天私人记忆深刻的意象进行书写。“暴雨过去以后,天空恢复明亮,我们穿着塑料凉鞋站在被改变了面貌的外部世界,水漫到小腿,垃圾和树叶一起漂浮,自行车破浪而行,我的父母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正骑车从单位往家赶。而这中间的一段时间是美好的空白,空气清洁,我和所有人一起停留在被水覆盖的宁静里。”
周嘉宁:用精妙语言表达心灵共振、情感、温柔
封面新闻: 我看有的作家谈创作,会提到他或者她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经验的缩减,在创作上会遇到题材匮乏的问题。对现在的你来说,寻找文学题材,“写什么”,是一个问题吗?
周嘉宁:我想我的同龄人如今普遍都是社会的活跃参与者或建造者。而在我35岁以后,无论是内部环境还是外部环境,都在剧烈而持续的变化中,但凡身处此浪潮中的创作者,我想只会面对扑面而来的经验,谁都躲不开。我在2018年出版《基本美》的时候,还在想着创作者要保持敏感以记录脚下地表最轻微的震荡或分裂。4年过去了,这些震荡与分裂已经大到任谁都忽视不了,同时也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时候题材绝对不会匮乏,但问题可能是如何在蔓延的阴影下寻找到可能存在的出口。
封面新闻:我看到你在创作谈文章里提到,“感谢姜亦朋姐姐在2020年夏天接受我的采访,我自此积累起《明日派对》的第一笔素材。”一般来说,让你写成一篇小说的契机、起因是什么?
周嘉宁:这三个小说每一个都在我心里待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它们各自最初的形态是如何的。2001年之前,我和很多当时的少年一样,是狂热的电台爱好者,即便到了高三我也因为听电台到凌晨而无法第二天赶上早操。姜亦朋的电台节目,曾伴随我度过了高中的一年。但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段更长的时间。
她的节目和其他一些节目一起,塑造了我最初世界版图的形状。我在成年以后与姜亦朋相识,得知当时电台给予她这档节目时,她还是在读大学生。我想,时代曾经给予青年最大程度的包容和支持,让他们能够将毫不确凿的声音传播到日渐坚固的城市里。
封面新闻: 在《再见日食》里,你写了一群年轻人参加文学写作营里发生的故事。在一篇创作谈里,你提到你有类似的真实经历,“2016年秋天,我和朋友们离开爱荷华,最终在纽约彻夜不眠玩了三天以后告别。第二年的8月,留在爱荷华的朋友开车去我们常去的林中湖泊看了日食。依然是夏日温暖的湖水,熟透的核桃,林间的小鹿。”所以,这个小说里应该有你和你的朋友们真实的影子吧?
周嘉宁:在《再见日食》的结尾那里,我通过主人公的对话说,“因为太好的事情根本舍不得让其他人知道。”离开爱荷华三年以后,我用文学的方式处理了爱荷华的记忆。但因为太好的事情根本舍不得让其他人知道,所以小说里的世界也只是处于虚构另一侧的世界,是记忆的投影。朋友曾说我在《再见日食》里终于写了爱情,我想我最初确实想要写一场美妙爱情,但最终写的却是新世界徐徐展开时候更为动人的情感,是好奇,冲撞,破裂和审慎。
封面新闻:在你的创作谈文章里,你写道:“所以在物理存在着的世界里,我从没有真正见过日食。但我见证过在日食时刻共振的心灵和情感,人类面对近乎永恒的自然发出的赞叹,以及随之而来的温柔。” 我觉得这几句话,非常精准表述了我在你作品里发现的最珍贵的东西——你的目的不是讲故事,也不是要塑造某个典型人物形象,而是用一种精妙的语言表达一群有相似经验的人的心灵共振、情感、温柔。
周嘉宁:谢谢你。我自己回答不好这个问题,我希望自己写作的意图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只存在于小说里,而不要脱离小说独立存在。有位朋友在《浪的景观》的读后感里说了一段很鼓励我的话:“周嘉宁之前的文字非常自我,到了《基本美》,文字明显转向了克制,它是清洁的、干燥的,每一次读都觉得好,感觉自己在阅读过程中变得洁净。也是从这篇小说开始,我觉得周嘉宁像从一个用文字拍电影的人变成了用文字拍纪录片的人。”
封面新闻:作家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时代、现实环境中。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容易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人吗?
周嘉宁:相比大环境本身,我更容易受到身处其中的具体个人的影响,人随环境而变幻的情感总是容易波及到我,在我周围形成漩涡。写作从某种意义上是对一切的回应,或者是向最深的黑洞发出的信号。但我自身是一个对内和对外都过分审慎的人,一方面使得我在环境中保持着某种一致性,某种内部秩序,另外一方面也使得我对时代的回应或者答复总有延时性。近几年来我和其他人一样,尽力生活在断裂中,也尽力收集崩塌中的碎片与残骸。
封面新闻:除了写作,你还翻译了很多文学作品。做文学翻译对自己写作的文字节奏、语感有怎样的帮助?
周嘉宁:翻译对我来说,除了保持日常生活不会失去秩序之外,也是对中文非常好的锻炼,不断在各种近义词之间做辨析,练习语言敏感度。我本身很爱汉字,象形文字在视觉方面的审美也与其他语言不同。我有时候觉得翻译对我来说是在“打捞和清洁”汉字。
封面新闻:不少人还是会提到曾经的新概念文学,青春叙事。你的作品里,“青春叙事”的气质其实一直在延续,并且随着写作技艺的提升,越来越具有艺术价值。对此您怎么看?
周嘉宁:创作对我来说是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碰撞以后产生的新世界,是自我的能量与外部能量的共振。我始终在探索和锤炼自己的能量,而作品是这个过程中的结晶体。
封面新闻:对文学写作的价值和意义,有信心吗?曾经有专职写作的青年作家跟我说,他在写长篇小说的过程中,会对自己的写作产生过怀疑或者虚无感。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周嘉宁:我从没质疑过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我也珍惜所有的自我怀疑和虚无感,无法相信一个没有自我怀疑的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