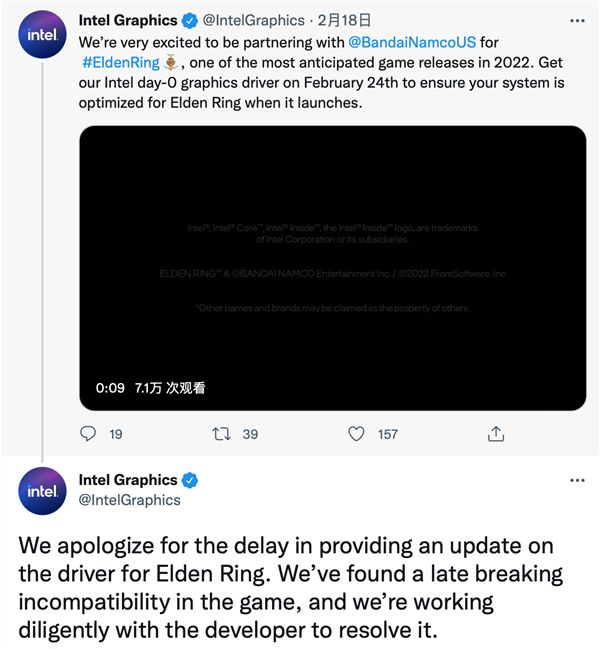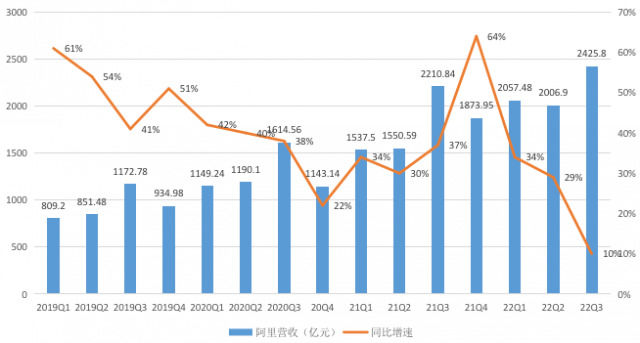我有一位网友,家在绍兴。某日,这位友人发帖说,如果有可能,他想把家搬到白马湖边的春晖中学,去和丰子恺、朱自清做邻居。这座百年名校就在绍兴东边的上虞——现属绍兴的一个区。从鲁迅的三味书屋出发到春晖,路程不到四十公里,搬过去不是没有可能。有留言问:你这是在物色“学区房”吗?比市区某校师资还好?

上世纪20年代初,春晖的“师资”全国闻名。夏丏尊、朱自清、李叔同、丰子恺,这一群质朴古雅的先生们,在春晖中学执教期间,于白马湖畔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作家群体,又称现代散文“白马湖派”。蔡元培、胡愈之、何香凝、俞平伯、柳亚子、黄宾虹、张大千等知名人士也被这里独特的磁场吸引,来此或讲学,或考察,推行新教育,传播新文化。那个年代是白马湖的“黄金年代”;那个时代,他们的语汇里还没有“学区房”、“鸡娃”和“内卷”,只有“人生三层楼”、“爱的教育”,和“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被他们的文学和人生理念滋养的学生后辈中也包括我。在我求知若渴的中学时代,课堂上喝到的“泉水”好像总带着一股漂白粉味儿,是在图书馆内偶然发现的一本《文心》——夏丏尊和叶圣陶先生用小说体写成的教学案例,带我真正尝到阅读和写作的兴味。
我忽然也想去白马湖看一看。所有说走就走的旅行都是长久心愿的累积。从北京乘高铁到杭州,再坐杭州开往绍兴的绿皮火车,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上虞。传说中,上虞是舜的出生地,也是祝英台的故里。适逢假期,曹娥庙、祝家庄等景区游人如织,而白马湖和春晖中学却隐居市井,既不刻意避客,也不故作逢迎。我为了去见它,还专门订做了一套民国学生装,蓝布斜扣上衣,丝光青色过膝裙,仿佛若不将自己的频率完全调回对应的年代,便无以舒展那沸腾已久的钦慕之情。
火车到站了,下车的人不过十几个,近乡情怯,不免忐忑。我认识白马湖,它认识我吗?
驿亭迎风记
旅途比想象中劳顿。没有直达春晖中学的车,我们抵达上虞火车站后,得先坐公交到上虞区内,再换乘郊区巴士。挤满鸡鸭鹅的小巴在乡间小路上晃荡了二十多分钟后,把我们甩在了一根与公路平行的铁道旁,这里就是驿亭了。驿亭是什么来头?朱自清在那堪称现代散文典范的《白马湖》中,几笔就写尽了——
“白马湖在甬绍铁道的驿亭站,是个极小极小的乡下地方。在北方说起这个名字,管保一百个人一百个人不知道。但那却是一个不坏的地方。这名字先就是一个不坏的名字。据说从前(宋时?)有个姓周的骑白马入湖仙去,所以有这个名字。这个故事也是一个不坏的故事。”
抬头一望,铁道那面的钢丝网上,小秋千架似的赫然挂着四个拙朴的大字:“春晖中学”,我顿时激动起来,一头准备扑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一辆高铁列车从鼻头前飞驰而过——护栏阻隔了我的兴致,也保住了我的性命。向双目瞪圆的道口工打听:穿过铁道,沿着湖边一条笔直的村道走上二十分钟,就是春晖了。
眼前这条煤渣铺成的村道似曾相识,因为它看起来和几十年前朱自清笔下的描绘并无二致。既然跟从前一样,我不可能比朱自清写得更好,索性任由那些几乎烂熟于胸的文字从脑海里蹦出来:
“白马湖并非圆圆的或方方的一个湖,如所想到的,这是曲曲折折大大小小许多湖的总名。……白马湖最大的,也是最好的一个,便是我们住过的屋的门前那一个。那个湖不算小,但湖口让两面的山包抄住了。……湖的尽里头,有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村落,叫做西徐岙,因为姓徐的多。这村落与外面本是不相通的,村里人要出来得撑船。后来春晖中学在湖边造了房子,这才造了两座玲珑的小木桥,筑起一道煤屑路,直通到驿亭车站。那是窄窄的一条人行路,蜿蜒曲折的,路上虽常不见人,走起来却不见寂寞——尤其在微雨的春天,一个初到的来客,他左顾右盼,是只有觉得热闹的。”
我们几个“初到的来客”,沿着驿亭通向春晖这段笔直的村道,顶着湖面刮来的五级以上大风,急急行进。要说这风,跟夏丏尊《白马湖之冬》里的描述也几乎是半点没差:“那里环湖都是山,而北面却有一个半里阔的空隙,好似故意张了袋口欢迎风来的样子。”顶风行走,必然谈不上享受,但淡雅的绿意融化入眼,农家采摘园里刚摘下来的樱桃入口,一路倒也优哉游哉。
可朱自清当年在这条路上就堪称奔波了。1924年,26岁的朱自清还在宁波的一所中学任教,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应春晖中学校长之邀前来兼课。每周四,朱自清从宁波坐火车到驿亭,周一再返回宁波,每周如此两地辗转。很多人不禁问道:佩弦啊,你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向往世外桃源的生活,但不一定非要到那里教书啊。在发表在校刊上的《春晖的一月》中,朱自清道出缘由:
“我看不出什么界线,因而也用不着什么防备,什么顾忌;……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一切事务,常常通力合作。……感情既无隔阂,事务自然都开诚布公,无所用其躲闪。学生因无须矫情饰伪,故甚活泼有意思。又因能顺全天性,不遭压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较纯正。”
城里人到了空旷的乡下,朱自清感觉到了一种“自然的美体”,而自由和真诚,才是春晖送给朱自清的两件更重要的礼物。上世纪90年代,《电视诗歌散文》这种节目形式曾经在电视荧幕上昙花一现。2003年中央电视台也曾来实地拍摄,制作了一期朱自清《白马湖》的电视散文。我也是在那年,考上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编导专业,希望今后能从事电视诗歌散文的创作。然而等到毕业时,电视荧幕已经被新闻、电视剧、综艺节目三分天下,我也半推半就地成为了一名新闻工作者。大风中,我开始用相机捕捉那蓄谋已久影像诗:前面那不就是朱自清的背影吗?他一手拿着教案,一手抱着父亲在月台送来的橘子,长衫飘飘,一步步走向春晖的黄金年代。
平屋奇遇记
走过一片稀疏的村舍,只见一排青瓦白墙的老房子静卧在湖湾旁的绿荫中。这就是当年春晖中学的教员宿舍了。从我们来的方向看过去第一间,是夏丏尊的平屋。不巧的是,学校正值假期,并未开放。一筹莫展之际,同行的朋友忽然想起来,单位有一位退休老领导是夏丏尊先生的后人。他立刻打电话回单位,让同事帮忙去职工宿舍老领导家敲门。不一会儿,只见一位老师骑着自行车朝我们的方向过来,在平屋面前掏出了钥匙——我知道,我的愿望又一次“得逞”了。来人是已从春晖中学退休的徐老师,家里还有一桌客人要招待,接到电话马上就赶过来了。我很是过意不去,连声称谢。徐老师看着我民国学生的打扮,“你这一身还挺像回事儿的!”脸上的焦急也开始转为笑意。
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夏丏尊是地道的上虞人,和他的老乡——绍兴人鲁迅一样,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后改为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教书。这所位于杭州的中学和北京大学遥相呼应,人才辈出,是当年新文化运动最活跃的阵地。其主张白话文教育,提倡学生自治,反对孔教礼仪,遭到守旧人士的不满,最终爆发了浙一师风潮。而当时浙一师的校长,是夏丏尊的另一位上虞同乡——经亨颐。风潮之后,经亨颐回到故乡,在侨商的赞助下创建了私立春晖中学,1922年正式开始招生。老校长振臂一呼,曾经的爱徒、挚交便携家带口纷至沓来,“北南开、南春晖”也从此传遍全国。
夏丏尊是最早来春晖的一批教员。初来此地的心情,都写进了他的《平屋杂文》:“当我移居的时候,还是一片荒野。……一家人于阴历十一月下旬从热闹的杭州移居这荒凉的山野,宛如投身于极带中。”刚从风潮中心中抽身的夏丏尊来到这山水之间,竭力想在其中寻求平静,遂按日本建筑风格设计自己的住所,并取名为“平屋”,寓“平淡、平凡”等意。
我们走进平屋中的一间,话不多的徐老师忽然指着一张书桌开口了:“夏丏尊先生就是在这张桌子前翻译完成的《爱的教育》。”丰子恺在给夏丏尊先生的悼念文章中写道,夏先生之所以会翻译《爱的教育》,因为他对学生也是一种“妈妈的教育”:学生逗狗吃酒他要管,生病失业他也要插手,但凡看见世间任何不真不美不善的事,都要发愁。人生实苦,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被他关照的人生命变得轻盈了,夏丏尊先生自己却因为某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感而忧愁了一辈子。
如今,平屋门前的路还是窄,不过屋后的荒地早已树木阴翳;这片绿油油的小树林冬可挡风、夏可遮雨,夏老的遗骸也长眠于此。原有的荒凉没有了,清净仍在,岂不最好?学生的读书声平日里也会远远传过石桥,传到平屋,一辈子致力于教育的夏丏尊先生,想必也不会再感到寂寞,不会再感到忧愁了吧?
法师助缘记
我总是误把弘一法师的学生,剃了头、留着长髯的丰子恺也当作出家人。虽然丰子恺一生佛缘甚深,但其实他并没有出过家;而叶圣陶散文《两法师》中的两位主人公,实际上也是弘一法师李叔同和马一浮。我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错觉,是因为他们的人生有太多交集,彼此的缘分嵌入太深,而其中重要的一段“共业”正是发生在春晖中学。
丰子恺还是浙一师学生的时候,夏丏尊和李叔同就是他的老师,1922年,丰子恺毕业后由夏丏尊推荐来到了春晖中学执教。他在白马湖畔的居所名叫“小杨柳屋”,也是当年白马湖作家群的一个“据点”。偶尔来春晖讲学的蔡元培、黄炎培、叶圣陶、张闻天等人,都喜欢到小杨柳屋聚谈,宛如一家。每逢丰子恺被众人怂恿作画,就会将一张八仙桌抬出,放在小天井的一棵杨柳树下,“小杨柳屋”因此得名。我并没有看到那张八仙桌,天井中的杨柳树也不复存焉,不过门前靠湖边的小路上是有几棵垂杨柳的,不知道是不是故人手植。“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丰子恺那被称为中国第一幅“漫画”的作品,既是白马湖“黄金时代”的标记,也暗示了某种结局。
“小杨柳屋”紧挨着的就是弘一法师的“晚晴山房”。早年留学日本的李叔同,回国后就在经亨颐的邀请下,在杭州任教音乐、美术,与时任国文教员的夏丏尊是同事和挚友。他最后决定出家正是来自夏丏尊的“助缘”。1916年夏日的一天,夏丏尊向李叔同介绍了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李叔同正想此法或能治愈他的神经衰弱,便悄然来到西湖边的虎跑,将断食付诸行动。两年之后,李叔同在虎跑寺剃度,正式皈依佛门。出家以后,弘一法师破席芒鞋,云游四方,修行逐渐精进,健康却每况愈下,让好友们心生怜爱。夏丏尊、丰子恺等人四处集资,1929年,为弘一法师修建的晚年居所在白马湖畔落成,新居结庐又值法师五十寿辰,法师手书了李商隐“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两句诗,从此便有了“晚晴山房”和“晚晴沙门”。
弘一法师是以夏丏尊好友的身份来到白马湖的,并没有在春晖中学担任教职,他整日独自静坐于山房,研习佛学或书画金石。有了“晚晴山房”,就仿佛有了某种寄托,这群精神气质相似的人,即使日后不在春晖教书,也经常回来拜访。在叶圣陶的记忆中,他们的聚会经常是少语甚至只是静坐默对,但已胜过十年晤谈:“晴秋的午前的时光在恬然的静默中经过,觉得有难言的美。”朱自清的绚丽、丰子恺的拙朴、夏丏尊的博爱、弘一法师的超然,彼此灵魂早就互相映照,何须再分佛门内外;文学、美学、佛学,生命的一切沉静的美好,一时间竟然绽放得如此全然。
借用电影《一代宗师》的台词:“所谓大时代,不过是一个选择。或去或留,我选择了留在我的年月。”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他们可以选择去抛头颅,洒热血,也可以选择偏居一隅,以教育“曲线救国”。
世事沧桑,晚晴山房在日寇侵华战乱中早成废墟,1994年,由新加坡广洽法师领头集资重建。如今的晚晴山房是故居群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也是唯一一所两层的建筑。站在二楼走廊上远眺白马湖全貌,多么希望过往的一切能重现——即使不是在白马湖,也可以是在别的什么湖边。但庭院空荡,徐老师在焦急地等着我下来。
春晖走马记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这首《游子吟》是春晖中学校名的由来,丰子恺为它配上了曲,如今仍是学校的校歌。春晖中学的遗址,今存一字楼、科学馆、图书馆、曲院等,各幢建筑均有长廊相连。电视剧《围城》中的湖南乡下的三闾大学,取景地就在春晖中学。走过一排整齐的水杉,就是三层楼高的曲院。红色木质结构,每间办公室门口,还挂了一小竖条木牌,上面用毛笔字体写着老师的名字。
经亨颐是一个游走在政治与教育中的人物,他参与过废光绪帝,位高曾至中央执行委员,也被开除过国民党党籍,最后还成了中共元老的廖承志的岳父。而白马湖的作家们,则纯粹是读书人的理想姿态。上世纪20年代初,社会风气未开,春晖却首开国内男女中学同校之先河。然而没过多久,经校长建议将男女生部分开,但夏丏尊先生和少数教师主合。虽然两人在私人关系上还维系着昔日的情谊,但在教育观念上却逐渐越走越远。一次乌毡帽事件,改写了春晖的校史。1924年,一位名叫黄源的学生从南京转学到春晖,一日戴上绍兴特有乌毡帽去上体操课,遭体育教员训斥,发生师生冲突。训育主任匡互生——就是那位五四学生运动火烧赵家楼第一人,不满教员压制学生的做法,辞职离校。夏丏尊、丰子恺、黄源等一干师生也离校前往上海,春晖的黄金时代由此一去不返。
1925年,立达学园在上海成立,夏丏尊、朱光潜、丰子恺、叶圣陶等人异地重聚,悉心教学与创作。为筹措学校经费,丰子恺还卖掉了“小杨柳屋”。上世纪30年代,他们又围聚在开明书店周围出版青少年读物,朱光潜的《谈美》,叶圣陶撰写、丰子恺绘图的《开明国语课本》,《中学生》杂志都是自那时诞生的。人在阵地在,哪管后来的文学史把他们称为“白马湖作家群”还是“开明”一派呢。
如今的春晖,建筑面积超过约10万平方米,拥有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中国十大名校等众多头衔。有意思的是学校还保留着手动的绳摇铃做摆设,不过平日报时还是用电子铃。
经亨颐曾说,“人生好比一碗清水,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健全的人格,以便使这碗清水发挥各种作用;功利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无论什么味的水,都有了局限……”这无色无味的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不就是这清澈可鉴心的白马湖吗?然而如今白马湖的面积萎缩了不少,湖的边缘一眼就能望尽。
如今的春晖还是昔日的春晖吗?学校还会为一位只教音乐、美术“副科”的丰子恺青眼相加吗?
送别
《长闲》、《白马湖书录》、《刹那》……别看朱自清为白马湖留下了这么多文章,其实他在这里待的时间不过一年。夏丏尊和丰子恺已率先离去,辗转彷徨之际,他接到了俞平伯的来信。1925年夏,朱自清最后一次沿着那条湖边煤屑路,穿过铁道,赶往北平清华园。
驿亭传来了火车的长哨,是时候打道回“京”了。也许是逛累了,我竟感觉那条煤屑路一眼望不到头,便在路边找了一户农家坐下来吃饭。白虾,花蛤,空心菜,加上一瓶黄酒会稽山。
当年浙一师新招音乐教员,有个人来应聘,第一句话就先提条件:必须给每位学生配备一架风琴。这个“耍大牌”的教员就是李叔同,而这个甘愿“认怂”的雇主正是经亨颐。他亲自出马,到处央求,把四五十架风琴凑齐。“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在经校长化缘得来的风琴上,李叔同演奏了自己写的《送别》。
驿亭,确实是个送别之地。1924年那场纷争后,匡互生也是沿着这条小路离开,同学们一直紧跟其后,含泪目送。著名导演谢晋,也是上世纪30年代就读于春晖中学的校友。2008年,为参加母校百年校庆,85岁的谢晋导演专程飞抵上虞,情绪激动又喝了点酒,没想到竟在酒店辞世。
斯人已往,何以怀念?“一刹那,是最可爱的一刹那,便是现在。事情已过,追想是无用的;事情未来,预想也是无用的;只有在事情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捉它,发展它,改正它,补充它:使它健全,谐和,成为完满的一段落,一历程。”原来,朱自清在白马湖旁写下的《刹那》,早就为我准备好了释怀的良药。